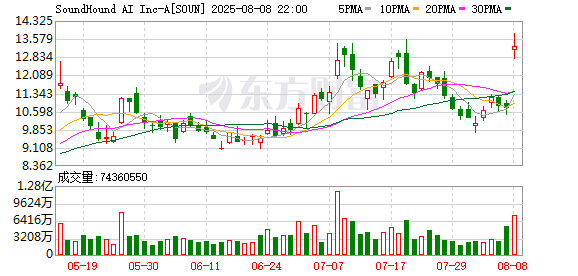(日)川北稔/文
2019年5月28日清晨,一群小学生在神奈川县川崎市多摩区登户车站附近等待校车。突然,一名50多岁的男子双手持刀冲了过去……在这起案件中,一名小学六年级的女孩和一名送孩子上学的父亲遇害,伤者人数达18名。
四天后的6月1日,一名住在东京都练马区的父亲(70多岁)用厨刀刺向了儿子(40多岁)的胸部等多处部位,起因是儿子嫌“运动会的声音太吵”而开始暴躁,儿子被送到医院后确认死亡。据说父亲向有关搜查人员透露,儿子曾有家庭暴力行为,并有蛰居倾向。他担心儿子会做出与川崎案件罪犯同样的事,所以杀了他。
川崎案件加害人与练马案件被害人的生活模式都接近于不上学、不上班、不社交、不进入社会,自我封闭的蛰居状态。此事曝光后,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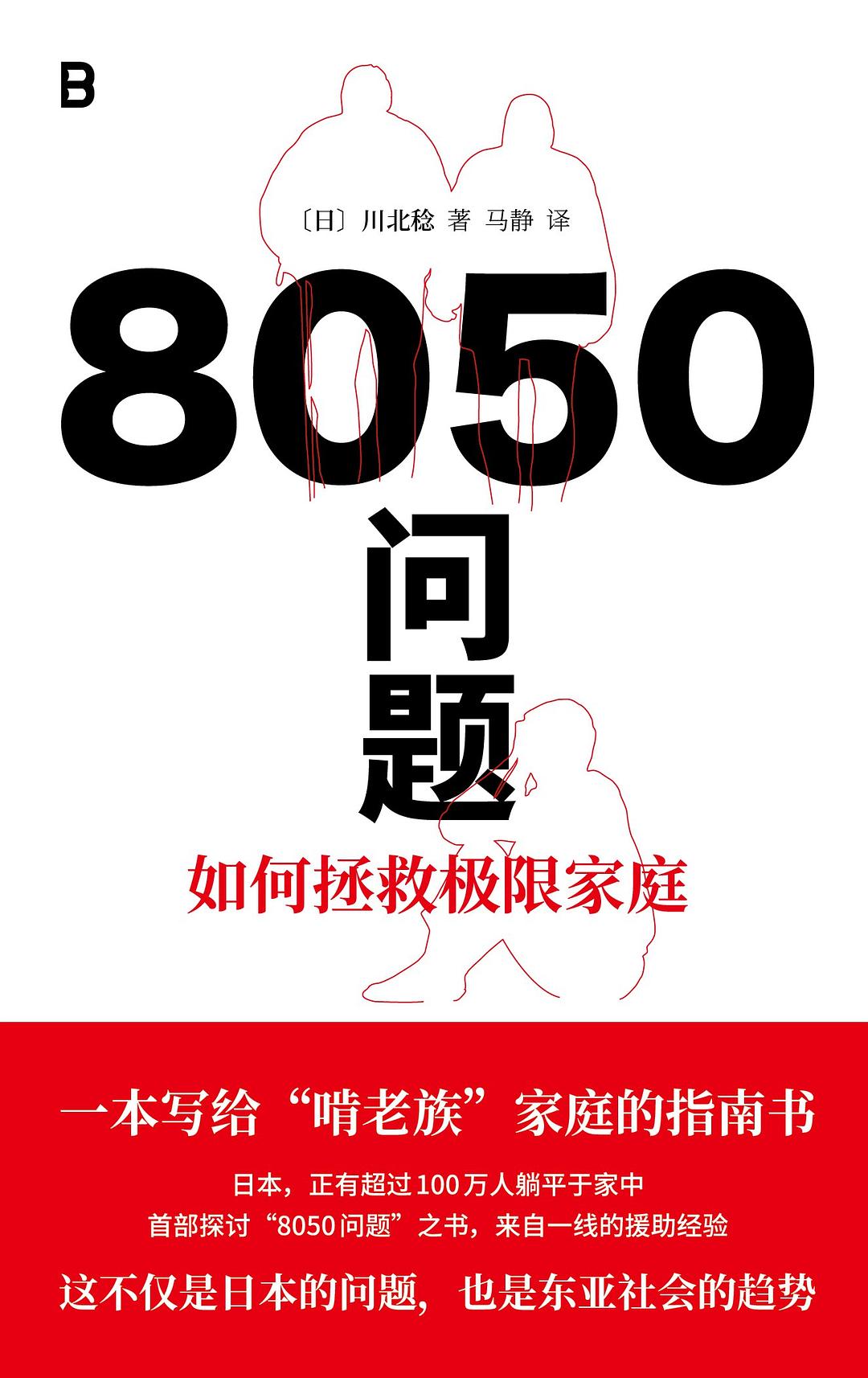
“8050问题”是指,80多岁的高龄父母与50多岁无业、蛰居的子女同住,他们在经济上陷入穷困,日益孤立于社会之外,这样的家庭在不断增加。本书将“8050问题”视为“高龄父母”和“壮年期子女”同住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具体来说,本书聚焦在拥有40岁以上子女且难以成为援助对象的家庭。
日本的老龄化将持续到2040年左右,不婚化也没有在同一时期好转的迹象。孤立家庭的增加,是应该正视的现实。
2016年,日本内阁府的调查显示,年龄在15岁到39岁之间的年轻群体中,处于蛰居状态的有54.1万人。由于此次调查将40岁以上的人排除在外,不少人呼吁“应该有很多中老年案例”“应该扩大调查对象的年龄范围”。为此,日本内阁府扩大了调查对象的年龄范围。2019年3月的调查显示,在全国范围内,年龄在40岁到64岁之间、处于蛰居状态的人口达到了61.3万人。这是首次将中老年群体纳入调查对象。从两次调查结果的总和来看,日本全国处于蛰居状态的人口超过了100万。蛰居问题也面临着长期化、老龄化问题,不容乐观。
在对40岁以上人群的调查里,由蛰居者本人维持生计的占29.8%,由父亲维持的占21.3%,母亲则占12.8%,由此可见,很多蛰居者本人会在经济上支持家庭。而在对39岁以下人群的调查中,由蛰居者本人主要来维持生计的仅占2%。
2003年,厚生劳动省发布了旧《“蛰居”应对指针》(最终版),从“生物学”“心理”“社会”等层面分别对蛰居背景进行了说明。
“生物学”层面,是指因患感统失调、抑郁症、强迫症、恐慌症等精神疾病而蛰居。这可能发生于蛰居之前,也可能因蛰居而产生。
另外,蛰居现象背后,也存在轻度的智力障碍、学习障碍、高功能广泛性发育障碍等。有人吐露,在学校生活中,自己不擅长某门特定的学科,即便擅长学习,却难以在休息时间与朋友聊天等。正因如此,他们在生活中经历了旁人难以察觉的艰辛,精神压力日益积累,继而陷入了蛰居状态。
“心理”层面是指,在蛰居状态开始之前就存在的精神压力,以及在蛰居状态下生活时本人所承受的紧张感和不安感。即使看起来像是突然变成了蛰居者,但或许之前他本人一直在忍耐。
就像人们常说的“优等生的窒息”一样,受到周围高度评价的人,有时会突然无法再上学或上班。另外,蛰居者本人诸如“别人会怎么看我”的焦虑会加剧,进而惧怕与他人交往。
从“社会”层面来看,在升学和就职等备受期待的人生转折点上,有时会遭遇挫折,未能顺利按照预想轨道前进。厚生劳动省在《指针》中指出,在只认可就学、就业的环境中,经历过蛰居的人想再次进入社会时,会面临很多困难。“要是蛰居,将来就完了”“不同于他人,这样不好”,若周围的人都用这样的眼光看待蛰居者,不仅是蛰居者本人,就连家人也会觉得蛰居“不妙”,是“坏事”,无法向外界寻求援助,变得越来越孤立。
通过实况调查和援助现场的实地调查,我感受到那些有蛰居子女的家庭,父母的困境在于“职责要持续到孩子几岁”“什么时候才能和子女分离”等问题,这与常见的家庭烦恼有相通的部分。随着人们的寿命变长,子女成年后,亲子关系持续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围绕亲子关系的烦恼也越来越多样。直至极限的家庭问题,既不是一览而过的新闻,也不是什么特殊事例。
日本的老龄化、不婚化继续推进,人口结构的改变使家庭所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人们对家庭的期待却越来越高。家庭中的问题很难和外界商量,练马案件证明了这一点。社会在变化,若仍然持续依赖旧有的家庭观念,很可能会加深家庭在社会上的孤立。
社会如何向孤立的家庭伸出援助之手?作为“父母”和“子女”,我们又该如何生活?我想通过本书和各位读者一起思考。(本文节选自川北稔著《8050问题:如何拯救极限家庭》,作者为日本爱知教育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还未登录
还未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