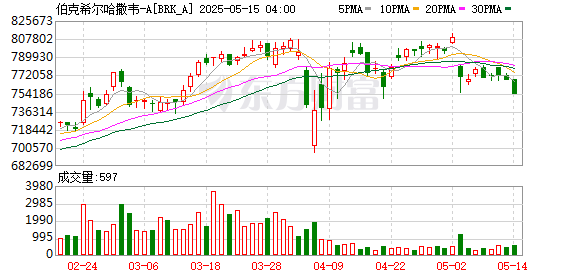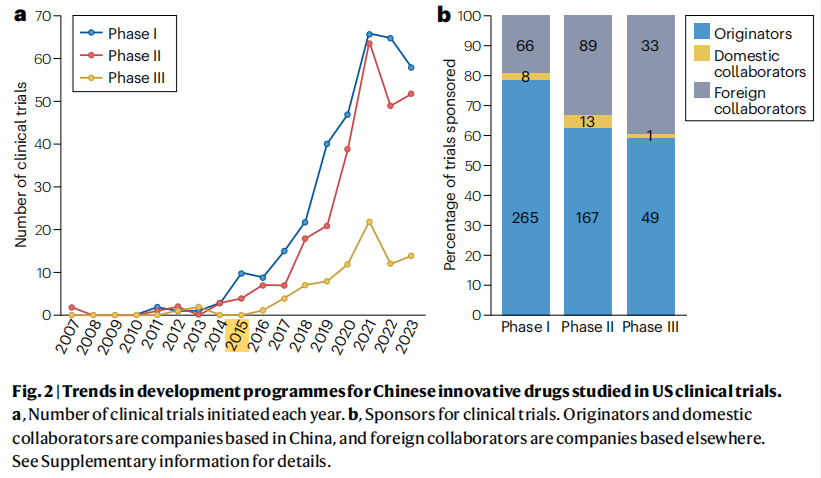4月底,西班牙突发了一场伊比利亚半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停电,由此引发人们对气候变暖趋势下能源转型的深层思考:在气候“沸腾时代”,人类电力系统正在向更清洁的新能源转换。但是,极端天气同样会给新能源的供应带来诸多不确定因素。从现在起,我们就该为应对这些“烤”验,思考更多、更全面的对策。
极端天气频频触动电力安全边界
4月28日,西班牙的电力系统突然出现大规模负荷流失,电网频率跌至47.5赫兹,由此触发电网自动保护机制。随后,伊比利亚半岛电网与欧洲大陆主网解列。紧接着,西班牙、葡萄牙超5000万民众突然陷入罕见的断电危机,交通中断、通信受阻、医疗系统崩溃,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直接经济损失超200亿欧元。
葡萄牙电网运营商曾提及事故可能与西班牙近期的极端气温变化有关,这透露出现代社会的能源系统可能正面临一些前所未遇的危机。
首先,高温热浪在极端天气事件中频率颇高,由此带来的用电需求激增,往往会打破电力的供需平衡,给电网带来严峻挑战。
从用户侧来看,极端高温使居民制冷、工业降温的用电需求呈指数级增长。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2018年研究,当气温超过30后,每升温1可使电力需求升高4%—6%。例如,2022年8月2日,上海在40高温红色预警下,电网最高负荷突破4000万千瓦,空调负荷占比达40%以上,单日用电量突破历史极值。
从电能供应侧来看,极端高温天气会对部分可再生能源的生产造成影响。例如,太阳能电池板表面温度每升高1,发电效率下降0.4%—0.5%。在45高温下,光伏系统实际出力可能比标称值低20%。又如,高温热浪事件往往伴随“极热无风”,这种天气条件会导致风电机组的发电能力大幅下降,甚至接近零发电,这会严重限制风电在高温用电中的调峰能力。
极端高温往往还会使电力设备稳定性面临极大压力。变压器是电力输送中的重要部件,每升温6,油浸式变压器中的绝缘纸老化速度就会翻倍。当变压器油温超过80,就将触发保护性停机。2019年,印度孟买大停电事故调查报告显示,当地多台变压器因长期在45高温下运行(油温达83),导致绝缘失效引发短路。
热胀冷缩是不可避免的物理规律,作为能源输送的“血管”,输电线路的导线也会在高温下膨胀——温度每升高10,典型档距下(200—400米)线路垂度将增加3%—5%。当极端高温来临,输电线可能因垂度过大而触碰到原本接触不到的植被,从而引发火灾。2018年,美国加州大停电的起因正是输电线路因高温下垂而引燃树木。
更值得注意的是,持续高温干旱形成的“火险三角”会让电力系统陷入两难。高温干旱会显著提升植被干燥度,使火灾季时间延长,大幅增加野火发生概率和过火面积。这又将导致输电线路的污闪跳闸、设备损毁等事故,显著降低其输电能力。
2018年,美国加州坎普山火就曾造成150余座输电塔烧毁。2020年澳大利亚山火则导致3.2万千米配电线路受损。2025年美国洛杉矶山火期间,部分区域因线路损坏和持续风灾反复断电。为避免野火引发的设备停运和损毁,电力公司被迫主动停电,致使数万用户受到停电影响,最长恢复时间达120小时。
构建更坚韧“自愈型”能源互联网
2023年7月,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表示:“全球变暖时代已经结束,全球沸腾时代到来。”这对全球气候变暖发出了新的警告。2024年,全球平均地表温度比1850—1900年平均值高出1.55(不确定性为±0.13),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根据联合国防灾减灾署发布的《灾害造成的人类损失2000—2019》报告,在2000—2019年的20年间,全球极端高温事件相比于1980—1999年增加了232%,洪涝灾害增加了134%,风暴增加了97%。
我们正处于一个温度升高、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沸腾时代”。除了高温热浪,极端大风、雨雪冰冻等各种极端天气都会让能源系统面临更多风险,维护其安全稳定运行的任务比以往更加艰巨。例如,2012年10月登陆美国的飓风桑迪带来的强风,导致纽约、新泽西等地区大量线路断线倒塌、变电站受损,造成约850万用户停电,部分地区停电时间长达数周,而电网修复费用高达数十亿美元。
在这场与极端天气事件的赛跑中,如何将危机转化为革新动力?目前,各国都在积极构建技术革新、系统重构与社会协同的三维防御体系,以保障极端天气下的电力供应。
例如,通过设备升级与智能调控,利用新材料、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提升电力设备耐高温性能、强化风险监控与预警、优化电网运行方式,构建坚强的网架结构,从而提升电力系统安全裕度。又如,通过电力电子技术与智能控制系统的深度融合,发展柔性电网与多源储能,以平抑负荷波动,从而应对负荷激增和极端天气等多重挑战。此外,通过地区间跨时空的协同管理,如北欧水电与南欧光伏通过欧洲电网的跨区互补,实现用电负荷的转移,并通过发展智慧微电网保障区域供电稳定。
当更富韧性的“自愈型”能源互联网构建成型,人类社会的重要“生命线”终可适应气候沸腾时代,推动人类文明继续前行。
(蔡泽林为云南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博士后,魏科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还未登录
还未登录